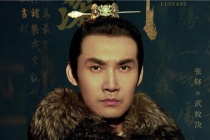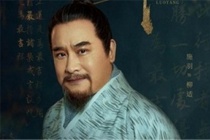欧阳修为什么不喜欢佛教
苏轼曾云:“(欧阳修)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诗书、学仁义之说者,必引而进之。”欧阳修并未因为佛门弟子的身份便对他们一味排斥,更多的是着重于看本人品格修养如何,是否肯定儒家思想,甚至是用儒家思想来改造佛教。就拿欧阳修与禅师契嵩的交往来说,明道年间,复古思潮涌动,不少文人学士都尊韩排佛。
契嵩为了针对当时排佛的浪潮,作《辅教篇》阐明儒佛两种不同宗教的思想本质,并上奏朝廷以反驳欧阳修等人的辟佛之说,轰动一时。然而欧阳修并没有因契嵩的反驳而不悦,反倒对其读书为文能通儒学、善古文而赞赏不已。不仅如此,契嵩的“以儒校之,则与其所谓五常仁义者,异号而一体耳”之句让欧阳修以为排佛理论得到了证实,喜不自胜地发出了“不意僧中有此郎也!”的赞叹。
又比如欧阳修与释惟俨的交往,庆历元年在《释惟俨文集序》中还用石曼卿的交友标准来衬托出释惟演的不俗,“惟俨非贤士不交,有不可其意,无贵贱,一切闭拒,绝去不少顾”,也借此说明了自己与之结交乃是出于交往贤士,并非是因其为佛门弟子。
这些个案均证明了欧阳修在与僧人的交往中并没有十分看重他们的僧人身份,反而着重于他们的品德和是否精通儒学。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并非完全否定佛道,正如王水照、崔铭在《欧阳修传:达者在纷争中的坚持》一书中认为的欧阳修并不是坚决的反佛斗士。从初至洛阳时不愿前去嵩山石室而被谢绛等人强拉至此,到后来多与僧人道长交往,可见后来欧阳修对佛道的态度已经开始缓和了。
但如果因此而认为欧阳修改变了排佛的初衷,晚年亲佛近佛的话,这也是不合理的。《新五代史》里欧阳修对佛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在他的笔下,佛教的存在对社会民生几乎是一无是处。在《原弊》一文里他更是强烈批判了佛门弟子不劳作却可以坐享其成的现状。
今坐华屋享美食而无事者,曰浮屠之民;仰衣食而养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时,南亩之民也。今之议者,以浮图并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国备,不可以去,浮图不可并周、孔,不言而易知,请试言兵戎之事。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今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
《原弊》僧人们依仗国家财政的支持不劳而获,这使得国家不仅丧失了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国家生产总值减少,并且因国家要支付僧人们的开支,更加紧了对底层民众的剥削,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农民辛苦耕作一年,却要上缴大量粮食来交赋税,遇到灾害之年更是食不果腹,而僧人们却在宽敞明亮佛家大堂里念经跪坐即可吃穿不愁,这在吸引更多人投向可以不劳而获的佛门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不仅如此,僧人们受到如此优渥的待遇却未必能安于本分,因为习惯了这种不劳而获的方式之后,僧人们容易变得自傲懒惰,而这对国家管理是极为不利的。欧阳修站在统治阶层的角度,兼顾国家大局,权衡利弊,关注民生,对佛门的不劳而获和渐生骄堕是十分反对的。
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的一生中在对佛道的态度上在公而言非常坚定,私下里却有些反复。究其原因,于公是因为佛道的存在给社会民生带来了负面影响,也阻碍了儒家道统思想的传播。于私而言,则是因为自洛阳与汪姓僧人辩论后,他开始接触佛家的精义,也开始以客观公允的眼光去看待佛道,在与僧人道长的结交中发现了他们尚品德、通儒学、善古文的优点,加之多年宦海浮沉、身心俱疲,晚年的欧阳修对佛道的态度有所缓和与退让。
-
上一篇: 翰林风月三千首写的是谁
-
下一篇: 欧阳修是否盗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