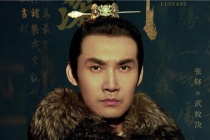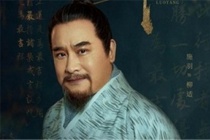陈寅恪失明后在助手帮助下完成鸿篇巨著
大概是因为同为世家背景,一位官宦子弟,一位富商千金,两人甫一见面就十分投缘,看重门风家教的陈寅恪与黄萱在气质上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加上黄萱拥有出众的国学才华,所以初次见面即受到大师的认可,并预感到黄萱是自己晚年学术生涯不可或缺的合作者。
一开始黄萱听不懂陈寅恪的口音,陈先生就耐心细致地解释说明,一反被世人认定的“怪癖、不好相处”的形象。两年后,黄女士通过了陈先生的严格考核,转为专职助教。
此时的史学大师,已经65岁。双目因多年眼疾,早就失明,身体又孱弱多病。但老先生壮志未酬,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按心中既定的规划目标,日夜兼程地从事学术撰著。
做为助教,黄女士遵从教授的需要,必须翻检多达六七百种的文史典籍,涉及到正史,野史,年谱,方志,诗话,戏曲,小说许许多多门类。
随便翻开《柳如是别传》,摘抄几句看看:“'乘搓拟入碧霞宮'者,自是指泛舟白龙潭而言。但李义山诗集上'碧城'三首之一,其句首云:'碧城十二曲阑干',注家相传以为'碧城'即碧霞之城。(见朱鹤龄注引道源语)义山此题之二,其首句云:'对影闻声已可怜',宋氏用以指河东君当时'影怜'之名。”
不多引证,仅这么几行,需要查找多少书目,可见一斑了。黄女士就这样一卷卷一册册一页页地寻找到指定的篇目,章节,段落,最后落实到具体的词句上。
进入写作成篇阶段,更是紧张。由于当时条件简陋,无录音机可用,陈先生就把酝酿成熟的腹稿,一句一句口述出来,黄女士则把口述内容,原原本本地记录在稿纸上。即使一个标点,一条注释,都必须做到一丝不苟,准确无误。
这就是黄萱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对面相处的是一位目盲多病的老夫子,与一堆堆纸页发黄的古书旧卷,沉闷单调,枯燥乏味。任务却繁重又繁琐。可黄女士不厌不烦,不停不辍,一做就是十三年。这是需要付出多少诚心、热心、细心、耐心的十三年,也是需要付出多少智力、毅力、精力和体力的十三年。
春华秋实。两个人十三年的协力耕耘,在陈老先生学术园地里,结出累累硕果。在此期间完成了《元白诗笺论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诸多鸿篇巨著。仅《柳如是别传》,洋洋洒洒八十多万言,三大册摞在一起,比两块砖头还要厚。这些学术力作,当然是教授陈先生的巨大贡献,但何尝不是助教黄女士的巨大贡献呢。
所以,在前面提到的“鉴定意见”里,陈寅恪说的“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的赞扬,绝不是溢美之辞,更以“惊天地泣鬼神”来概括她的这位“寅师”晚年的不朽功绩。虽然陈寅恪一直是和她平辈论交,以“黄先生”相称,并要求子女称呼“周伯母”。
然而,写这个“意见”的时候,“黄先生”54岁,9年后,63岁的“黄先生”退休,职称仍是助教。从1952年算起,黄先生在中山大学整整做了21年助教。21年,只是助教。黄女士不图虚名,不计薪水,把最好的年华和心思全扑在协助完成陈先生的著作上。
在学术世界里,如果把陈寅恪比作是朵艳丽的大红花,那么,黄萱连绿叶也配不上,最多算是花枝下面一丛小草。可是,这“小草”,却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当得了的。一位弱女子显示出的精神境界,概括为通常说的“牺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
上一篇: 梁启超与陈寅恪的争与不争
-
下一篇: 宇文化及当了多久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