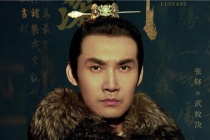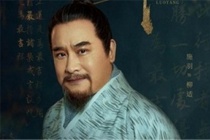陈寅恪和唐筼的爱情故事
来到伦敦之后,英国最著名的眼科专家斯图尔特·杜克-埃尔德亲自主刀,给陈寅恪做了两次手术。手术之后,他的视力终是复明无望。陈寅恪,一个著书立文的学者,失去了眼睛,他以何为业呢?没人能承受这样的打击。他凄然落笔,“去年病目今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此后的日子,据其女儿的回忆,唐筼除了“照顾失明的父亲生活起居外,还担负起书记官的任务,随时记录父亲要写的书信、诗作等”,建国初的二十年,政治运动迭起,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他的各种“声明”、“抗议书”,乃至“文革”中的所有“交代材料”全出自唐筼手笔。
1962年,陈寅恪在家洗漱时不慎摔倒,导致右腿股骨骨折。更糟糕的是,随后的保守治疗导致其股骨再也无法长合,此后余生只能长卧于床上。陈寅恪暮年曾对身边的人说:“一个人没有了眼睛等于没有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命,没有了腿,等于连另外的百分之五十也少了一半。”
壮年盲目,暮年膑足,命运带给一个自负、自傲与清高的生命,怎样的一种凌辱!幸运的是,在那段风雨漂摇、贫病交加的岁月,有知书达理的妻子陪伴在身边,唐筼亲历亲为,甘为丈夫遮风避雨。她以孱弱的身躯抵挡密集的箭矢,为他争得一片稍可喘息的空间,而自己的心脏病也日趋严重。
失明之后,陈寅恪仍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有时为了第二天一个要修改的小地方,陈寅恪一夜都不敢睡,一直牢牢记着,直到助手黄萱第二天清晨来叩门。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在十余年里写出近百万字的著述,这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1969年10月,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陈寅恪死后,唐筼出奇地平静,甚至没流下一滴泪。她没有让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随他而去,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结束。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筼,最终亦为陈寅恪而死。
陈寅恪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唐筼作为一位北洋新女性,德才兼备,却在遇到陈寅恪之后,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将自身的生命完全沉浸在柴米油盐和照顾家人的私人领域了,生死相随。爱到这种程度,爱到这种境界,让快餐式爱情的现代人汗颜。
陈寅恪曾提出“五等爱情论”: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出于理想,“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这样的爱情现实中是没有的,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才能发现。
二等,“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若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合,也为其忠贞不渝,如贾宝玉与林黛玉等。
三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爱了,也有过肌肤之亲,然后就再也放不下了,如司琪和潘又安。
四等,“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这才是人们平常最多见的,这样的婚姻生活以平淡为基调,以稳定为最高准则。
五等,“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对于见一个看上一个的花心大萝卜,这样的感情已经不能称为爱了,是对爱的亵渎。
若依陈寅恪的爱情等级分类,他与唐筼的爱情不过区区四等,但唐筼的作为,爱到为他生,为他死,却生生提到了一等爱情,“甘之为死”。
-
上一篇: 陈寅恪是哪里人
-
下一篇: 陈寅恪的四不讲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