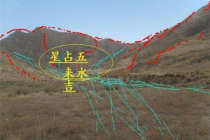文人画的历史发展
钱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墨而飞,不尔便入邪道,愈工愈远。””又引申为:“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都重视把书法的笔墨情趣引入绘画,勾勒线条亦具文人的典雅风格。
在元代绘画实践上,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
其代表人物倪云林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人画论:“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倪瓒:《题为张以中画竹》)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明代
明代初年画家分为两派:一派始忠于宋元文人画的传统;另一派是复古派,即明初复兴的皇家画院中继承南宋“马夏”院体山水画传统的戴进、吴伟等人。但“吴门派”为代表的明代文人画,扫除了“复辟”的“院体”画,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风格推向更高一个阶段,其主要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与仇英。吴派画家的主要成员大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他们敏感或切身体验到仕途的险恶,于是淡于仕进,优游林下,以诗文书画自娱,他们尚意趣、精笔墨、继承“士气”的元人绘画传统,表现自己的品格情怀。
晚明张宏一出,拓展了文人山水画新的境界。至此,文人画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已发展成熟,而张宏则予以总结和创新,遂使以文人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张宏之于绘画的最大影响,在于他重视继承古代人的笔墨传统,把对风格的追求作为艺术的重要目的。而且,由于他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有各自的美学追求,从而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张宏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手法,对后来画坛有很大影响。涌现出一批师法自然,重视写生的优秀画家。
约自万历至崇祯(1628~1644)年间绘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徐渭进一步完善了花鸟画的大写意画法。陈洪绶、崔子忠、丁云鹏等开创了变形人物画法。以张宏为代表的苏州画家在文人山水画方面另辟蹊径,创作出了富有生活气息的绘画作品。他们在继承吴门画派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回归自然,到大山里去写生,师自然造化,悟出了绘画的真谛。在画中体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使山水画活了起来。
张宏的写生论及其师法自然地绘画实践,哺育了明清一大批山水画家,其中佼佼者,当为画史所称的石涛、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为代表的革新派,还有四王和吴恽等画家。四王和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绘画虽有区别,但都是为了表现各自的笔墨趣味和独特个性,因而,四王和石涛都是文人画内部的两条路子,一条是从创作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中国绘画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一条路是继续进行笔墨的艺术实验与大胆革新,以求进一步发展,两者皆有显著的历史功绩,体现了变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清代
清代到文人画鼎盛的时期,涌现了诸多顶极文人画家,最突出的是“四僧”,“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石涛最为突出。身为明末遗民,他们在书画中寄寓国破家亡之痛,八大笔法恣肆、放纵、简括、凝练,造形夸张,意境冷寂。石涛努力体察自然,鄙视陈陈相因,亦步亦趋的画家,主张“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主张对后世的“扬州八怪”(“扬州画派”)、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