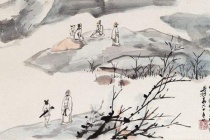西晋时期佛教的发展
总之,西晋一代的佛典翻译,大概是受本土玄学影响太重,其中加入了大量玄学概念、词汇,不仅不利于佛典原义的表达,又难以为一般人理解,这大概就是后世研诵此时期翻译出的经典者不多的根本原因。也是东晋后,佛教界出现多次关于重要典籍、重要佛学名词之辩论的原因。
西晋的佛教传播,在民间仍停留在建寺供僧求福报的层面,当时已出现手抄的“供养经”,敦煌曾出土的《宝梁经》,土峪沟出土的《诸佛要集经》即属此类。对于士大夫们来说,佛法的弘扬仍旧偏于学术研究、文字功夫,至于真正有心法传承,真为解脱生死而入实修者,基本未见于文献记载中。
从学术界的记载来看,当时的学佛人,主要以翻译、研习、讲解经典为弘法。其实真正的信仰者应当明白,佛法是心法,若无佛陀一代代口耳相传下来的心法传承,靠研读佛典求解脱根本就是本末倒置:释迦牟尼佛因实修成道后才演说的三藏十二部,不是通过研习经论而成佛的。有因缘的人,一听相应佛经,当下明了就当下解脱。若因缘不契,纵使读遍千经万论,讲解义理天花乱坠,也与解脱成佛无关。反而因给人们造成了“修行就是研习佛典义理,讲经即是弘法度生”的错觉,成为魔业。自己尚未解脱,怎么能翻译涉及甚深见地的了义经典?怎么能讲经弘法?若自未解脱,必不能令他人解脱,此时讲经不是弘法,是行魔业!
佛教发展至西晋,翻译事业更盛,译出经典更多,信仰者也相当普遍。据法琳《辨正论》记载,当时洛阳、长安的寺院就有百余处,僧尼共三千余人。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佛教进一步发展壮大了。但从正法的弘扬看,这些除了与众生结缘,保留下一些佛典文献,对于实修,对于众生的解脱毫无意义。
而且,由于在译经、讲经过程中,晋代的玄学概念、语言太多的渗入,反而给众生造成了许多错误概念,尤其是对“般若”、“空性”等名词的误解,直接障碍众生的解脱。这些涉及甚深见地的内容,本来是超越言语的,只有依止明了者,通过心法传承的加持,才能真正明白。所以说,西晋佛教的发展仍是正法传入的准备阶段。